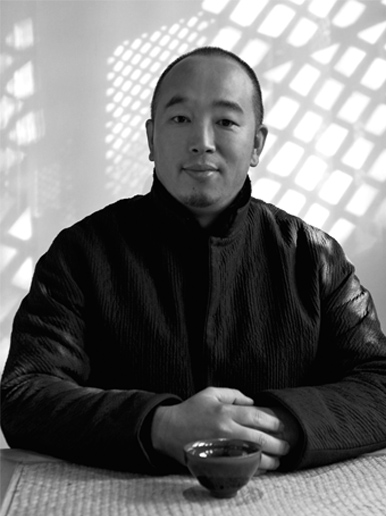1974年出生,199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致力于室内设计与景观设计事业的发展,曾多次任职国内重大工程设计项目的总设计师,作品获得社会的高度关注和专业褒奖。仲松是见证中国设计快速发展的一代人,无论作为设计师或者个人,他坚持“设计以人为本”,专注社会阶层设计差距的研究;同时他主张应通过重新定义、理解中国文化的过去以探索中国设计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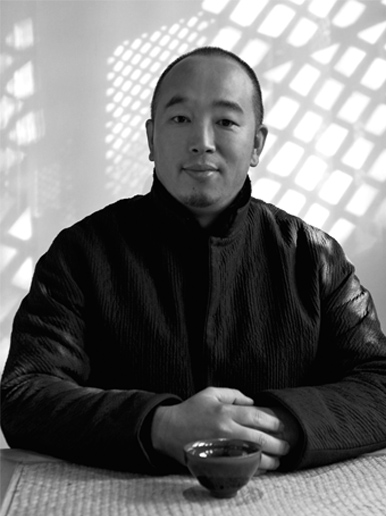
仲松
仲松
北京仲松建筑景观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设计总监
采访/周红 摄影/叶建荣
宁波装饰:设计师都比较有个性,相对于70年代的当代艺术家,在大家的眼中您比较特立独行,事实是这样吗?
仲松:我只不过是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被太多的约定俗成的东西所限制。我们生下来,从孩子到成人到进入社会,会有一系列教育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在剥削你独立思考能力。如果那个东西在一开始就觉得理所应当,就不会去问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认为是好的。我不是说这种规则不好,我们尊重这种规则,但从我个人来讲,应该要有一定的思维自由,而这种自由是一种不断反思和自省的精神。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从中找到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你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传播出去,不是你自己独强,而是你的责任,这才是有价值的,不在乎你做设计还是做金融。
宁波装饰:您曾经说过“我们去阅读一个建筑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关注设计的本身,更多的要去了解背后的故事。”在您看来,怎样的设计才称得上好设计?
仲松:我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国家大剧刚刚建成时,大家都在争论这个充满现代感的设计与天安门附近传统风格的建筑群“格格不入”。我的观点是,我们没必要讨论国家大剧院,应该讨论的是旁边的建筑物——人民大会堂,因为从设计理念本身来讲,人民大会堂是一个很糟糕的建筑物,它是一个外来殖民地政治行为的建筑,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特征。但是今天我们去看人民大会堂,不仅是把它当作建筑看,我们会从这个建筑加了自己的内容之后再去看,我认为这就发展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设计本身的认识,不是说把图纸画出来了,你就可以成为设计师,一定是要建造起来,而这个建筑能延续到结束,而且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人去评论,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急于一时去对建筑做评论呢?
宁波装饰:在您看来,什么才是最具备价值?
仲松:整个过程才是最有价值。如果我们只关心其中一段,而我们关心的那一段无非就是攀比,这样会出现奇怪的建筑,就是说我们非得把建筑做成那样?当然也可能是需要做成那样。但问题是,他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除了解决这个城市的人、群体自身的虚荣心以外,更多是解决实施这个建筑和参与这个建筑设计师本身的虚荣心,这是我经常反思的。
宁波装饰:在您的很多作品中会体现本土化元素,请您谈谈在这方面的创作体会。
仲松:我特别注意这种刻意,尽量希望在一个自然流露的状态去使用一些典型的符号。你做设计,很快会通过一种方法和实践出来一个习惯,然后形成我们所说的风格,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讲,首先不应该被一种风格所固定下来,甚至是追求某一种固定的风格,我觉得这是愚蠢的事情。我比较倾向“无法之法,无由定法”,不要去被一种固定的、相似的东西束缚住,但是我认为好的设计做到合适,就是恰到好处,不过分设计,但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只是在说我认为的原则而已。
宁波装饰:对于中国一些高端项目,本土化设计的体现情况怎样?
仲松:现在有很多客户越来越多关注本土化,不管是表象还是深层次,他们有这样一个需求。我觉得这是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很明显的一个变化,说明这是一种趋势。作为当下,中国人在这些已有条件里,不管别人说我们有钱也好,暴发户也好,大家急于找到这种依托点,这个依托点就是我们要回到传统本身所留下的一种价值,大家会去关注这些价值。
宁波装饰: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项目会选择国外设计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外国设计师在中国文化的理解上或者是在中国本土化设计的掌握上表现怎样?
仲松:这有一个发展过程,在2003年到2004年间有一个大爆发期,这期间中国所有重要项目由国外设计师囊括。这是因为客户市场对于自身行业或者是本土设计师没有信心。很多人会反思,到底中国建筑师有没有自身的价值?回答是肯定有的,如中国建筑师王澍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这是国内外很多人梦想的奖项。王澍得奖后,给很多主流设计师和即将成为主流的设计师们很大的冲击,其实他们很在乎这种奖项。第二,是给即将成为设计师的学生一个很大触动,原来大家会学很多知名的国外设计师,把他们当作神一样膜拜。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原来不够冷静,我们真正本土化的设计师,像王澍,在本土可能默默无闻,在国际上却成为了主流,这是一个很滑稽的结果,值得我们深思。所以不要去相信权威,或者被所谓的这种权威或者势力所改变。
 您现在的位置: 宁波装饰网 > 人物访谈 > 正文
您现在的位置: 宁波装饰网 > 人物访谈 > 正文